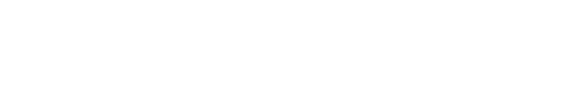4月16日下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翟学伟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作“本土学术概念的提出和建构:以人情与面子为例”的学术讲座。此讲座是研究院“学思讲坛”系列学术活动的第二讲,由夏正江教授、范为桥教授与谈,王洁教授主持。翟教授的讲演涉及建构本土概念的意义、本土概念的类型和特点、建构的艰辛过程,蕴含着一位学者建构社会学本土话语体系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下为讲座实录,内容略有改动。本文为上篇。

图 翟学伟教授
王洁(主持人):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相信在海报发布后,各位同学老师应该都看了翟老师的一些著作或文章。30年来,翟老师一直在独立思考和研究如何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探索提出本土的概念和理论。其实我们之前是不认识翟老师的,只不过是在书上、杂志上看到了翟老师,然后跟华峰商量给翟老写一封电邮,邀请翟老师过来做一次讲座。我们中心在张民选老师的引导下做TALIS、PISA研究,包括做TALIS的Video Study,以及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很多的经验,但是如何建构本土的教育学概念,如何向世界的教育学贡献中国的理论,还任重道远。我很期待翟老师能给我们一点引导和启发。我们首先请翟老师讲,之后请夏正江教授和范为桥教授来跟翟老师进行一些讨论。然后同学们也可以提一些问题,翟老师您看好不好?
翟学伟:好,没问题!非常感谢,虽然没有学校或者老师之间的网络,或者说没有人情面子的连接,但是我意外在邮箱中看到了你们发给我的邀请。说实话,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选择走这样一条路是中国学者应该承担的一个事业。一切关心这个事业的机构对我发出邀请,我都应该积极参与。因为这个话题不是一个人能做成的事情,应该是许多人共同来思考的问题,而我特别想促成这件事情能够走得更远,这就是我的初衷。所以我一看到邀请就很高兴,很愿意到这里来和大家一起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在我来的路上,接我的学生提了一个小问题:我当时是怎么想到在30年前去研究这个问题的?我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进入到今天的话题里面去。我是1987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30年应该有了。社会学真正恢复是1979年,但是要到高校里面设置专业、培养人才,中间还要经历几年。所以我也算是最早的、恢复社会学以后考上研究生的一个普通人。
刚刚王老师说她教过三年的中学,我也教过三年的中学。我最早学的是英语专业,也是在师范读的。我觉得英语专业最好的优势就是谈西方,不需要通过中文来转译,可以有机会直接读英文的书,然后在中国可以大行其道,就能把借助中文谈西方的人甩的很远。我们都把这些情况看成是好的情况,但也是个很糟糕的情况。为什么呢?
语言如果是一门工具的话,我们只是想拿这个工具去做事,严格上讲我没有受过任何其他领域的训练。你如果到理工科,会受到很严格的训练;如果你考到社会科学里面,不管是经济学、心理学还是到教育学,也有训练,因此本科就是一个被受过训练的人。受过训练的人怎么好呢?他本科就开始学这个专业了,到了研究生就已经有从事研究的可能性了。但是我们学外语专业毕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今天回头想,可能就因为我当年什么都没有,就没有觉得这个学科里面的大佬们把自己压的喘不过气来。当时社会学刚恢复,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搞。我们在同一起跑线上学社会学,有的热爱西方社会学,但是我并没有那么热爱,差别只是这么一点点。但是不热爱不是一个情绪的反应,而要想怎么能够把你的思考和研究做到跟西方社会学一样的好,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事。
追随西方社会学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坚定不移地信,认为他们做得真好。在我的讲解中我也会提到,他们的的确确做的好,这个要承认——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西方社会科学的产生,再到今天,他们做得很成功。第二种人是什么样呢?是那些对西方提供的观点,包括理论和方法经常表示怀疑,但又没有办法做得更好的人。这种人就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跟在西方后面。这样也挺好,至少学界认可你,或者在崇尚西方的大前提下做一点小的变动,这一变好像自己的东西就出来了。这种小敲小打的东西在中国学界的各个口子里面都有。
我这个人呢,不想沿着西方的道路走。这种胆量是谁给我的呢?我作为一个研究生,肯定没有这个胆量,也是受学者启发的。那时候北京刚刚建立起来的心理学协会,请了一个香港大学的高级讲师杨中芳到大陆做一个社会心理学发展方向的报告。这个香港学者跟随台湾学术已经开始发起了关于“社会与行为科学中国化”的讨论,后来改成“本土化”。她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又在美国的高校里面教过书,然后又回到香港。
我现在跟她经常联系。我问过她,你当时是去讲演了吗?她说没有,其实当时就是写了一个讲稿,递到会上让别人去读的,自己没有去。虽然我不在那个会上,但是这个讲稿被传出来了,我在研究生宿舍里面看到了这个讲稿。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时并不是老师的一堂课非常重要,不是一门课非常重要,不是你选择了一个专业非常重要,而可能就是某个老师讲的一句话非常重要,可能就是一个观点很重要。有的时候,你在课堂上没学到什么,而学校搞了一个讲座,突然就让你觉得某个东西特别得重要。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的时候,这本讲演稿传到了宿舍,我意外地在串门中看到了这本讲稿《试谈大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我一看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马上开始看这篇文章。我一看完,我当时就决定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它为什么能吸引我呢?倒不是说它讲了一番大道理、喊了一些口号吸引了我,完全不是。相反,它讲得很朴实。比如说大陆现在要恢复社会心理学,那没有恢复时候的社会心理学是什么呢?是苏联的社会心理学。今天讲这个话,你们可能会感到很陌生,但是八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要么没有,要么就是翻译苏联的社会心理学。大陆改革开放后,我们想学美国的社会心理学。我们拿一本苏联的社会心理学,看里面的章节目录,再拿一本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看里面的章节目录,虽然都叫社会心理学,但里面讨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苏联人眼中的社会心理学应该讨论这些问题,而美国人眼中的社会心理学应该讨论那些问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社会心理学下面没有一个统一的可讨论的内容,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民族都能在里面建立自己要讨论的内容。我一听这个话对呀!如果说全社会的社会心理学体系都是一样的,那么苏联人写一本书跟美国人写一本书,里面的内容也应该一样的。但明明都叫社会心理学,怎么会不一样呢?既然不一样,中国人也可以搞一本社会心理学,跟苏联不一样,跟美国也不一样。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既然存在“中国社会心理学”自己的内容,那我再去找什么是中国社会心理学能谈的话题,这就找到了“人情”和“面子”。因为人情和面子苏联人不会谈,美国人也不会谈,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懂,这不就是一个我可以谈的话题吗?所以我的起步是从这开始的。
所以我以后各式各样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把“面子”的研究做完之后,慢慢地延展出来的。如果我没有下工夫在“面子”的研究上,是没有办法再去做其他研究的。所以今天我以“人情”和“面子”的概念为例,让大家看我是怎么做的,希望对你们有启发。
我的这个做法虽然是三十年前的,但是没有想到在三十年后仍能吸引到人。我最近开了两次会议,讲了我当年是怎么做的,竟然依然可以在重要期刊上发表。我暗中大吃一惊,说明三十年前的东西没有过时。
我最近参加了几个关于社会学方法的小型会议,因为社会学再不谈方法也已经不行了。我们之前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全部是西方的,“中国社会”、“中国人”在社会学中只能被当作研究对象,现在慢慢觉得中国能不能产生概念呢?走到了这一步,然后再慢慢地问中国人能不能搞点理论呢?很多人就不敢想了。再下面一步,要搞这个理论用什么方法去建构它呢?那完全又是一个新的三十年。
首先我们知道,概念是学科或者叫科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在西方人看来,如果一个学科没有概念,那么这个学科是不成立的,或者说概念是一个学科研究的最小单位。一门学科或者一门学科中的某一个理论是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概念组合而成的。那么我又想——有没有一些学科并不介意概念的重要性呢?其实想想还是有的,可能我讲的不对,比如说历史学。因为我硕士读的是社会学,但后来拿的是史学博士,再后来又是南大心理系主任,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些学科各自的特点。历史学为了还原历史,找证据,搞考据、考证,它通常会在一些人物事件里面做非常艰巨的资料挖掘、资料整理的工作,对概念的重要性不大关注。当然这是传统史学,当史学有一天想向社会科学靠拢的时候,它也会意识到概念很重要。
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最后都会意识到概念的重要性。非常丰富的生活,一旦变成一个概念,你就觉得自己本来要说很多的话没有了。如果你不用这个概念,你有许多的故事要讲,许多的现象要描述,很多表格要做——当你突然发现这里面用一个概念能表达的时候,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但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概念才是开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遇到的一个问题——古希腊、罗马发展出来的理性思维里,他们意识到了概念的重要性,但是中国从《易经》过来的这种社会文化,认为“意象”非常重要,“意义”的“意”,“象征”的“象”。中国人是跟着意象走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没有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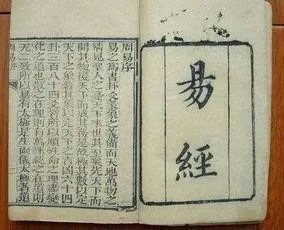
图《易经》(图源自网络)
西方人有概念,他们是在概念的基础上做研究的;中国人有概念,但是由于是沿着“意象”走的,就导致了即使中国有概念,但中国人不知道定义很重要,不知道内涵很重要,也不知道外延很重要,甚至我们的学生博士毕业了,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概念的定义,以及概念的定义中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直接借一个西方的概念,别人只要对概念有疑问,他一句话就挡开了:这个概念不是我提的,我只是拿过来在中国做了一个测量和调查而已,你为何对我的概念攻击这么多呢?就这样避过了一劫。
我现在审一些心理学稿件,看下来基本上全部是这么做的:这个论文要研究一个概念,然后直接找一本西方的书、论文,搬过来引一引,如果有三个西方人讲的不一样,那就引三个,再把这三个一组合,三个合成一个,全部都有了。但是,人家三个学者的概念原本是争论的,他一组合,综合地非常好,争论没有了。这些逻辑问题我们都没有系统训练。比如概念为什么在西方变成了一个学科的基础,而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概念当作概念,而只停留在“意象”上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西方能够在概念上做很多事,但我们都做不了。比如说西方人能够从现象通过概括得到概念,然后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他就能够在思想的层面或理论的层面上讨论问题。我们这方面能力就比较缺乏。另外西方人发明了概念之后,首先是在数学里面,他可以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来构成一个命题,然后他再把若干个命题组合成一个模型,甚至是扩张为一个体系,这都是西方人特别擅长做的。但是我们这样的思维训练很少。
我刚刚讲的是从自然科学到哲学这个层面。西方的实证主义发展出来之后,又有一个很聪明的做法——让概念操作化——让这个概念变得可以测量。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能测量呢?那就是在定义的时候,定义成一个可操作的定义。通过大量的问题设计还原到对这个概念的经验性把握上。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是思辨的把握,是一个经验性的把握。
很多情况下,如果一个理论流派有了一组概念以后,通常里面会出现一个核心概念,或者叫标志性的概念。那么这个理论流派就会用这个标志性的概念作为他理论流派的名称,就有在学界打出这个理论旗号的可能性。
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说西方人很好地处理了概念,那我们中国这边怎么办?这是我们今天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刚刚说,中国有自己的概念,但是中国没有形成逻辑以及对概念逻辑上的要求。人都是有逻辑思维的,但是把逻辑变成一个学科来研究逻辑是什么,以及逻辑在表达人的思维方式的清晰度,以及它的推演、归纳、三段论,以及我们经常所说的悖论,都是西方人提供的。我们不少研究生非常缺乏逻辑训练,这使得在科学意义上做创造的可能性较弱,或很容易被人家一挑战,就觉得根本立不住,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借考研究生的机会,把《形式逻辑》这门课给补过了,意外摸到了西方的思维训练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偶然性。
我们要搞本土概念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问题,因为概念需要逻辑。所以现在我要分几个层面给大家说一说。首先不能因为中国或者中国的文化里面缺乏逻辑,我们就放弃对本土概念的寻找和追求。为什么不能放弃?第一点是本土概念能够帮助我们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你用了一堆洋人的概念,抽象度是够的,概括度是够的,但是它往往不接地气,进入不到你的生活。有了本土概念以后会怎么样呢?会对中国人的生活理解方面更进一步,比如“人际关系”就是一个概念,而且是一个西方社会心理学里面很重要的概念。但是一旦想研究中国人的关系,去大量了解西方关于人际关系的理论之后,你已经失去了研究中国人关系的可能,因为它已经把你带跑了。看起来,有的西方概念很贴切中国情境,你以为这个概念能帮助你进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时候。但是并没有。所以建立本土概念就是换一个角度进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我们把这个角度称之为本土化的视角,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研究贴合的需要。一旦我们有了本土概念,就会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非常接近。一个东西好像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能够处处感受到它,但是我从来没有从学术上考虑过它,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它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只是跟着它走,跟着感觉走,但是从来没有在理性上认识过它。但是当你有了一个本土概念的时候,它能够让你站在学术角度上把一个你熟悉的生活看得很清楚,这一点我待会儿介绍人情面子的时候,会讲得比较清楚。
第三个是理论建构的需要。如果你想在中国搞一些理论,那么理论的基础,按照西方的要求它的最小单位就是概念。一旦要想在中国搞自己的理论,连概念都没有建立,怎么敢去想理论上的事呢?可见,建构中国人自己的理论首先需要建构本土的概念。
但是本土概念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一旦它逻辑没有的时候,它的意象性出来了。用意象性去看本土概念,我认为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模糊性,我认为这是本土概念类型中的第一种情况:传统思想中提出的经典概念及其实践。刚刚讲中国有自己的概念,比如“仁义礼智信”。这几个概念没有逻辑分类,而且儒家几乎也没有定义什么是“仁”,即使你把《论语》读完了,也没有定义“仁”是什么,而且孔子在不同的地方对“仁”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那到底以哪个为准呢?受西方的影响,你说不行,没有定义我理解不了。那么我们是否按照西方的框架,到《论语》里,把几个“仁”的定义地方都挑出来,然后你自己找一个最能够反映“仁”的意思,其他就不要了。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中国的概念不能做西方式的处理。

图 《论语》中的“仁”(图源自网络)
我在研究中还发现,中国人往往用否定来寻找肯定,这在逻辑中是不允许的,但在中国我们就这么用。比如说这是一个杯子,西方人要求直接定义这个杯子,但我不定义这个杯子,我只是说“它不”,它不是方的,它不是扁的,它不是黑的,它不是一种单一的颜色。所有的“不”讲完,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西方的逻辑是让你直接从正面说,你就直接说它是什么不就完了嘛。
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了,中国概念这么模糊,这个定义怎么得到呢?我觉得中国人很聪明,不下定义,在模糊的时候反复对比,让你在对比中领悟基本含义。到《论语》中去找“君子”的定义是什么,你是找不到的,但是孔子每次说“君子”的时候都带上“小人”,一会儿说说“君子”,一会儿说说“小人”。如果你是“小人”你这么干,你要是“君子”就不会这么干,你要是“君子”就会这么干,你要是“小人”,你不可能这么干。这么来来回回,你大概也能在比较中来获得对一个概念、一个含义的把握,这是可能的。
我觉得在讲本土概念的时候,有一个中心与边缘的含义。这带来什么结果呢?会带来重叠性。比如说我是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西方人就会说这是甲和乙,A和B。A不是B,B不是A。中国人是什么样呢?我拉着你的手,你摸着我的心,我是我,但是我也连到了你;你是你,你又连着我。用中国的土话讲,“咱俩谁跟谁呀?”咱俩虽然分不出谁跟谁,但是还是有名有姓的谁跟谁。所以中国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很多人研究中国人的“自我”都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他拿了一个西方的“自我”概念来进行研究。西方“自我”概念的前提就是它的独立性,个体不能独立它怎么会有自我呢?但是我们中国人又想谈“自我”,又要谈不独立的“自我”。那就是说,我这个“自我”跟别人的“自我”有重叠的部分,我在谈“自我”的时候已经谈到你那去了,但是又不完全是你。
西方人在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里面,当说A的时候,跟B就没关系,当你把A说完了说B,就跟A没关系。中国是个阴阳太极图,你说的A里面还有一个圆点,已经涉及B了;你觉得该说B了,里面还留个圆点,还是有A在里面。但是得承认,它的确有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有重点和非重点,也就是有一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仁义礼智信”就是一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仁”里面有“义”,“义”里面有“礼”,“仁义”里面有“礼”,“礼”当中有“仁义”。所以当你拼命研究中国的“礼”,你意外懂得了中国的“仁”和“义”;拼命研究中国的“仁”,你又意外地明白了什么是“礼”——它们都是有关系的。讲“仁”的时候它会涉及到“礼”,但是它的中心还是在讲“仁”,它的边缘已经涉及到了“义”和“礼”,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传统的经典概念,没有想过用逻辑去对待这些概念。但今天你又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训练,那你就面临着怎么来处理中国经典的、传统的概念的问题。

图 太极(图源自网络)
本土概念的第二个类型,我认为是日常生活用语的提炼。老百姓平常说话,说到最后,你会觉得里面一个词特别重要。每当中国人遇到事情都喜欢用这个词,就会发现这个词是用来解开老百姓生活的一个很核心的词。那我们怎么把这个词变成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难度比上面那个传统思想难度还要大。
日常概念危险在什么地方?人人都懂。面子在中国会有人不懂它吗?没有人不懂。但问题是人人都懂的东西,你敢去研究它,被否掉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你讲个我不懂的我就听着,但你讲个我懂的,一个我天天都遇到的东西,你在那神乎其神、夸夸其谈,我越听越觉得怎么一个我天天都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感受到的东西,怎么被你一讲,我完全都不认识了。那反对的人就特别多。
用日常生活语言去提炼一个概念,你要特别熟悉这个词汇,还要有能力陌生化这个词汇,有能力去抽象这个词汇,把它抽象到符合使用人意愿的地步。这种能力就是已经抽象到可以用这个概念来分析社会,而这个日常用语别人用了一辈子,也没有能力用来分析这个社会。“人情”、“面子”就符合这样的条件。中国人“人情”使用频率特别高,“面子”也一样,又是日常生活用语,每个人都觉得他只要活在这个社会,都明白什么是人情面子,你要把他这个看似明白说的让他不明白了,那也许就解释不了他的日常行为了;可你要是说的只让他明白,那你自己水平也不够。你要说的他尽管觉得明白,但是让他发现自己没这样想过,这里面有很多文章要做,而你讲一讲更清楚了,还让他很受启发,觉得搞一个理论出来是可能的,这样才行。比如说“过日子”,这个词在中国用得就非常频繁,所有人没有想过要拿它来做概念,但是中国有一个学者,他在哈佛念书的时候想研究自杀,他觉得西方人讲自杀用的是宗教的概念,也特别复杂。他觉得中国人也自杀,但是都不是西方找到的这些概念和原因,最后一想中国人的自杀多数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中国的土话,夫妻间用的最常见的话——“这日子没法过了”——这就是他想死的原因。他抓住了这个东西,中国人的一个本土概念:“过日子”。要把它提炼成一个学术语言,要跟西方的自杀去对话难度也很大。
本土概念的第三种类型是什么呢?是需要学者自己去创造。如果觉得中国社会有一个现象,中国社会有一个特征,怎么去表达它好?你既没有用传统的经典概念,又没有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去,你便想创造一个概念。今天学界想做这个事的人很多。比如说在哲学里面,李泽厚提个概念叫“情本体”,他想用“情本体”来反映中国哲学的特点,这就是他创造的一个概念。

图 李泽厚(1930—)(图源自网络)
社会学的“差序格局”也是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中国经典文献中没有,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但是费老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结构格局、亲疏远近弄到一起,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人类学里面也有很多,比如在比较中美文化差异的时候,许烺光(编者注:行为科学家,心理人类学创始人之一)就提出了“情境中心”和“个人中心”的概念。许烺光认为中国是一个情境中心的社会,情境中心社会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人所在的场景比人本身要重要。

图 费孝通先生(1910-2005)和许烺光先生(1909-1999)(图源自网络)
在许烺光的这对概念中,人的生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管到任何地方,我就是我,那你就突出了自我。还有一种生活是我要看情况,看什么情况?看谁在谁不在,谁比谁大,更狠的人在不在等;或者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说话场合,是在大庭广众下说的话,还是在私底下该说的话。一件事能不能做,能不能说,都是由情境来决定的。所以要想认识一个人就变得很困难,因为通常他要看情境来决定他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这种现象一个定义叫“情境中心”。
当然我们提出这对概念的人也会小心翼翼,不能够因此得出美国人是没有情境的,中国人到处都是情境。许烺光曾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美国人请吃饭就是情境中心。什么意思呢?两个人下班后,一个人说:“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把地点跟另一个人说了后,他说:“好的,但是我一定回家一趟。”回家干嘛,回家换衣服。中国人是穿一身衣服走到哪都一样,吃饭去就是了,穿什么有什么意义呢。我之前去美国,我们所在的代表团有一天的计划是上午逛公园,下午参观美国最高法院。在中国人看来,出门就是看看今天多少度,穿好衣服到哪儿都行。但当时被告知需要把下午的衣服准备好。上午玩过回到车上把领带打好才可以参观法院。这就是一个情境——你到什么情境,你的行为要发生改变。但是就算你观察到这一点,依然可以认为中国是“情境中心”的,而美国很适合用“个人中心”这个词。西方的油画是一幅个人中心的画,永远只画一个上半身,头那么大;中国国画中的人远远的、小小的,茅草屋里面探个头,也认不得他是谁,然后周围云雾缭绕,山山水水。这也是一个情境中心的审美。
我前两天刚刚从福建回来,我和同事参观集美大学,在校园里互相拍照,我每次给他拍完,他都要拿手机检查一下,说后面的楼,人家是两层楼,你不把顶拍出来人家就以为这是五层楼,十层楼。你一定要退远一点,一拍上面有天,大家才知道这是两层楼。背景很重要,说明我来过什么地方,关键要拍这个景,这就是“情境中心”。你要找西方人拍照片,任何的景一概不管,上去就对着脸一拍。这就是个人中心带来的,他认为你自己知道在哪就行了,拍照片主要是拍人。除非你明确说是风景照,我就给你拍风景。
人类学家的敏锐度、观察力也是非常好的,有的时候超过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也会提出很多创造性的概念,比如说为了解决东西方的自我差异,心理学家就提出来一个“独立我”和“互依我”。所以当你觉得现有的概念不能够帮助你来实现你要做的研究时,你真的能提出一个能站得住的概念,让大家觉得这个概念提的好,有助于我们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很多现象,那你就成功了。
总体上,我个人认为本土概念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点,在中国的任何概念里面,想找定义都是没有的。本土概念没有定义。严重到什么程度?连费老的“差序格局”都没有定义,都是我们后人帮他做了一些定义。而我们帮他做定义也不知道这个定义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假如费老这个概念自己定义过了,我们也就不吵了。问题是中国人自己不定义,有概念也不定义。我认为自己创造的概念,自己是可以定义的。因为生活中的概念你去定义别人会反对你,传统的概念都已经被说了两三千年,乱给它下定义跟古人思想也不相符,但是自己造的概念可以定义。
第二个就是语境的重要性。这个跟汉字的演化有关。中国字原来单字特别多。英语里面有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中国连介词也没有。英语有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有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西方人搞得很明白。但在我们中国,一个词你可以说它能当名词用,可以当动词用,可以及物,可以不及物,也可以当形容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词的把握是在语境中把握的,这个也给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和人的思想带来了非常多的复杂性。因为我刚刚说过中国概念的确定有一个比较的特征,也使得许多词汇有其对应性,比如“阴”和“阳”,想知道“阴”我们来谈“阳”;谈“小人”,我们来谈“君子”;要谈“利”,我们来谈“义”,我们就是在这个比较中来确定它的定义。

图 讲座现场